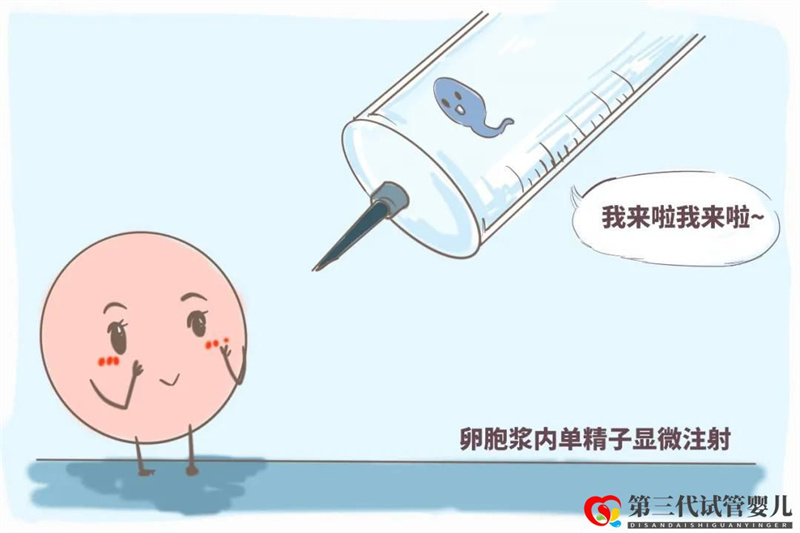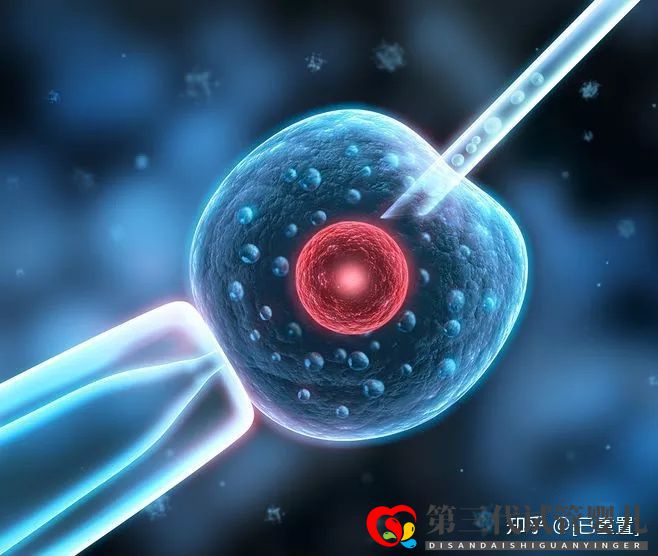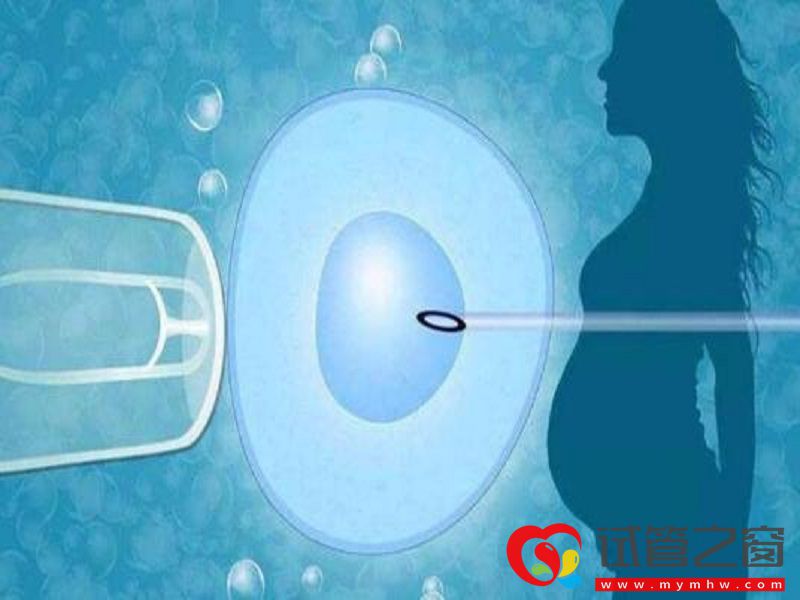認識佛醫:臨終前的病苦,可以避免嗎?


《尚書·洪范》中的五福六極,是上古先民對三世因果之理最樸素的認知,壽、富、康寧、攸好德、考終命“五福臨門”也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對幸福美好人生的基本定義。尤其是考終命——無疾而終享盡天年,即所謂善終,是人們直面生死時秉持的終極愿望。
被念佛人列入每日朝暮課誦中的《西方發愿文》,則把“考終命”這個心愿描述的更加周詳:“稽首西方安樂國,接引眾生大導師。我今發愿愿往生,唯愿慈悲哀攝受……至于臨欲命終,預知時至。身無一切病苦厄難,心無一切貪戀迷惑。諸根悅豫,正念分明。舍報安詳,如入禪定……”
每一個信愿念佛人,命終之后的歸宿都必定是阿彌陀佛極樂世界,翻開《凈土圣賢錄》數千往生傳記,無一不是在闡明這一事實。然而,在臨終之前,他們中既有纏綿病榻者,也有安詳自在者,種種差別不可具說。那臨終前的病苦,是可以避免的嗎?《西方發愿文》中身無一切病苦厄難的心愿,需要如何實現?
乘佛力故,稍有病苦
廬山優曇和尚所集《蓮宗寶鑒》中云:“慈照宗主凈土十門告誡云:凡夫雖有信心念佛,緣為宿業障重合墮地獄,乘佛力故,于床枕間將輕換重。若也因病苦故悔悟身心當生凈土也。無智之人不了此事,卻言,我今念佛又有病苦,反謗彌陀。因此一念惡心徑入地獄。此是一關也。”
1936年,印光大師76歲,應邀赴上海護國息災法會主持大悲佛七道場,并說法七日。是時會中有一青年名叫宋允中,隨眾皈依于大師座下,得名真根,此時年僅21歲。
八年后,居士病重將死,感嘆“病苦甚,西歸何日”。來看望他的陳海量居士為作開導,“前世惡業重,今世凈業輕者,則于命終前受諸病苦,以消惡業,命終徑生極樂。若前世惡業輕,今世凈業重,則命終前無復病苦。此視人之能勤修凈業與否也。故佛徒臨終病苦,正是重報輕受,往生前之好消息”。居士聽聞后心開意解念佛不輟,后見金光滿室,西方三圣降臨接引,居士遂合掌稱大勢至菩薩一聲而逝。
宋允中居士,幼好繪事。年十三,父玉麟先生,命從名畫家杭精英先生學。居士具藝術天才、攻讀復勤、所造深邃。杭先生信佛,居士受熏陶。二十五年冬,印光大師說法于上海護國息災法會,杭先生率居士及同學輩,乞大師授三歸,居士得法名真根,時年二十一。茹素念佛,早晚功課,歸心凈域。年二十六,與李夢花女士結婚,于功德林素筵宴客。夢花女士從之信佛,伉麗情篤,前歲居士病肺,住醫院,近二載,去肋骨七,顧未愈。乃家居養疴,念佛彌勤。入冬以來,病漸危篤。本年十月二十八日,余往慰問。居士曰,病苦甚,西歸何日。余曰昔玄奘法師,臨終亦病苦,有天人告云,法師于無量劫來,損惱眾生之罪業,今仗三寶力,轉為輕受,于此病苦中盡了之矣。居士之病,亦復如是。彌陀大愿有云:“十方世界,諸天人民,前世行惡,聞我名號,懺悔為善,奪持經戒,愿生我剎,壽終不經三惡道,徑遂來生。”以是前世惡業重,今世凈業輕者,則于命終前受諸病苦,以消惡業,命終徑生極樂。若前世惡業輕,今世凈業重,則命終前無復病苦。此視人之能勤修凈業與否也。故佛徒臨終病苦,正是重報輕受,往生前之好消息,世人不解,輒致疑惑,誠誤矣。所謂前世今世來世,亦猶昨日今明日耳。此身為前世善惡之業力所驅使而來,報未盡,焉能去。如人有事于此,事未畢,胡能他往。又如獄囚,期未滿,胡能出獄。此身,獄也。神識,囚犯也。囚期若滿,繼愿留獄中,亦不可得。此生業報一盡,靈識去矣,留不可得。居士安心以待,持念佛號毋忘。余復告其眷屬曰,生必有死,亦猶晝必有夜,循環往復,孰能免者。壽縱百歲,終當別離。所惜死后,各隨業受報而去,會見無期,為足悲耳。今玉麟先生,及賢眷屬,皆能精進念佛,則此后共往極樂世界,永作法侶,無復別離,是則舍此報身,方當慶幸,復何悲耶。訪問既竟,余乃別去。是日下午十時,其家人咸就寢息。居士呼曰,起起,余將西歸,幸為助念。家人環榻誦佛號。居士拍手稱阿彌陀佛,囑家人隨念。久之,見金光滿室,西方三圣降臨接引,居士遂合掌稱大勢至菩薩一聲而逝,時二十九日上午一時也。越三日就殮,舉身柔軟,見者嘆異。居士全家沐佛化,介弟允恭,今年十八,畢業于電信學院,奉佛尤精進。居士,江蘇嘉定人,寓上海南市董家渡街二零二號,世壽二十九。(1944年農歷十一月十八日陳海量記 《往生凈土見聞錄》 )
欲免病苦,精進念佛
信愿念佛的人,臨終稍有病苦,這正是乘佛力故重罪輕受,屆時不可心中狐疑。若欲得免病苦,須在平日精進凈業,用功念佛。
實際上,不僅僅是病苦,了然法師在《入香光室》中發問:“凡我等念佛行人,應當考實今時凈土法門,與古時凈土法門,究竟是異耶,同耶。若言是異,我等歷歲經年,從朝至暮,所稱佛號,皆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,而與古時佛名,絲毫無別。若言是同,云何古人生西,個個特別容易,不生則已,生則驚天動地。上輩往生,臨終佛來接引,天樂百千,幢幡無數,白鶴飛翔,異香滿室。人人可見,個個可聞。要去即去, 去亦不須人助。坐脫立亡,任隨其意。下至普通行人,皆能預知時至,沐浴更衣,端坐念佛,見佛來迎見佛色身,安詳而逝。逐一思之,令人可慕。云何今人生西,十有七難。縱然得生,非常勉強,必須人助。考其臨終瑞相,許多上輩往生,不及古時中下。況中下輩,更不必言。……我等應當究其古人所得,得在何處。今人所失,失在何處。”
了然法師又云, “今人往生,十有七難者,皆由缺乏定善之力,專靠散善功德,信愿回向故也。縱得往生,多屬勉強。古時行人, 根機深厚。除散善外,無論修觀,持名,皆能得定。是以千即千生,百即百生。不生則已,生則瑞相昭著,去時自由。” 所謂古人臨終,無有業縛,解脫自由者,皆因平時修持功夫得力。所謂今人所失者,失在平時修持功夫不得力。
諦閑大師力宏臺宗兼修凈土,與印光大師相知相交三十多年,印光大師最初未開許給居士授皈依前,往往令皈依諦閑大師。1931年,諦閑法師春夏間,在上海玉佛寺講楞嚴經,復應無錫居士請,為講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。因年高時至,炎熱過勞,講畢,即示疾。回寧波觀宗寺后,精神日就疲乏,乃息心休養,每日唯佛是念唯凈土是歸。雖無任何痛苦,而飲食日減,身體日弱。1932年夏,諦閑大師即將觀宗寺一切事權,交付妥當,令門人寶靜等繼續弘持。至七月初二日午前,忽向西合掌,良久云,佛來接引,老人將從此辭。旋喚侍者,用香湯沐浴更衣。續索筆寫偈云:我經念佛,凈土現前,真實受用,愿各勉旃。寫畢。繼命寺眾齊集大殿念佛。復令人扶行,趺坐龕中。適見皈依弟子方志梵在側,以所念念珠,從容付還之。午后一時三刻,目張而視,視而復閉。于大眾念佛聲中,安詳含笑而逝。面色光潔,頂暖逾時不散。
印光大師知悉諦公往生后,寫下《挽諦閑大師》:“猗歟諦公 乘愿示生 大張教網 我何能名 愿受佛記 速返娑婆 普度含識 同生極樂 ”。
方圣照居士來信報告諦公往生情形,大師回信要為諦公朝暮課誦回向一七,并不無遺憾地說:“諦公之逝,的確往生。其去之景象,尚不至驚天動地者,以講說時多,專用凈功時少也。在常人如此,則頗不易得。在諦公則猶未能副其身分。”
祖師大德們為法忘軀,損己利人。若知而不修及修而不專心致志,不唯辜負深恩,且何可消大業障于現世去世,臨終不免種種病緣之所逼迫。
南無阿彌陀佛
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
南無清凈大海眾菩薩
普愿沉溺諸眾生
速往無量光佛剎